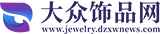数千年民族文化的淳酿——写意梅花
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文化在几千年中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大一统的前提下。中国的士大夫始终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接受了“君权神授”观念下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君臣、父子、夫妻、男女等方面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忠孝、礼义、清正等道德戒律。也许,中国士大夫中的“君子”们始终没有弄懂,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文化从来就是处于尖锐对立之中的。事实上,维系几千年封建专制机器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利益关系,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就是这部庞大的政治机器中的互相倾轧而又互相依存的“齿轮和螃经钉”。在封建社会里,君子是不屑于为衣食小事而忙碌的,这就产生了人类社会史上的一种独特的“君子远疱厨”现象。“君子”,即恪守道德的士大夫和文化人,他们既是社会的得益者,同时又是它的道德上的批判者。因而,他们始终是统治集团的边缘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士大夫以及知识分子们边缘人地位的绝妙写照,然而,由于前者常常只是对于“天道”、“明君”的一种消极的等待,故后者便是其唯一可行之道了。“独善其身”的含义是追求个人自身心智的完美,它包括哲学上的玄谈,政治上的谤议、道德上的无为和琴棋书画的自娱,而在客观上则产生了丰富的精神产品--艺术,包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册作为其心智追求和个性表现的《历代梅花写意画风》
梅花与松、竹并称“岁寒三友”,象征着孤傲、坚贞的人格和高雅、脱俗的情趣。显然,这是基于梅花的自然品质而产生的一种借喻。梅画的作者,多为仕途失意的士大夫。清未著名画家吴昌硕的一首咏梅诗,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士大夫心态:“冰肌铁骨绝世姿,世间桃李安得知”。这便是画家们偏爱梅花的原因,也是以梅入画的作品的基调。不过基调并不等于主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时千余年,数十位画家的梅花写意画之精品,千姿百态,风格各异,意韵丰富,不可一概而论。而决定题材选择的原因并不能决定主题。某种艺术欣赏恰恰要放弃对于主题的探究。在这类艺术品中主题就像一件旅游纪念品,不是旅游因纪念品而有意义,而是纪念品因旅游而有意义。在时过境迁的今天,某些艺术品淡化主题的态度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种纯艺术的欣赏,感觉作品本身的意味或“意韵”并理解其在人类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资料图】
【资料图】
就绘画艺术形式来看“写意”一词绝妙地概括了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本画册所选作品均在宋代以后,而宋代正是“写意”原则确立的阶段.所谓“写意”,即以意为主,重表现而轻模仿,讲“意境”而不重实写。把物象的“人品”象征放在首要地位,而把客观物象的形象放在次要地位、艺术品中的客观物象的形貌,不过是创造意境的手段,是表现思想,感情的导体或媒介。所以似与不似都无所谓,只有意境,人品等等,才是绘画的根本。一言以蔽之,“写意”的要旨,就是发人之意,品正味纯,“画中有诗”。然而绘画毕竟不同于诗歌。我们不妨把“画中有诗”理解为不必拘泥于自然的一种艺术自觉。写意画中的梅花,不是自然中梅花的写照,也不仅止于梅花的主观印象,而是将对象消化于意象之中,将其分解、玩味、组合,重构“成竹于胸”,然后作于纸上。可见,写意画超越了写实主义和印象派(主义)自称的“表现主义”而实际上是发人意、诗情为主的结构主义。我并非认为西方艺术的发展落后于中国千余年,每一民族的艺术发展各有其独特历程,每一种艺术创造方式都可能产生卓越的艺术品,因此,艺术的发展是历时的,但艺术品的价值是共时的。中国就意象形式看,它相似于中国的书法,文字被分解、变形、重构,并通过刚柔疾徐,抑扬顿挫的笔法处理,以至于使之不再是一种语言符号,而成为一种呈现于视觉的艺术符号,其意味早已溢出了语义。
再谈画梅,在所有的绘画题材中,梅花也许是最具抽象性的,很接近于俄国画家康定斯基所追求的音乐抽象性。就构成单元来看,内容不出花、枝,但花为点,枝作线,却构成了一曲曲拨动心弦的曲谱。当然,这仅仅是比喻,不可走得太远。绘画毕竟是视觉艺术。因此,对于梅花写意画来说,我们可以借结构主义的方法,探讨梅花画面构成的可能性,以及不同的构成将产生怎样的情感效果,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无背景的,亦即纯艺术的欣赏状态;既不考虑梅花的自然品质及其象征意义,也不考虑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作者的遭遇、性格等背景。事实上,这些背景对于我们的艺术欣赏毫无用处,在这些历时地产生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出任何观念和技法形式的前后相续的变化,从艺术的角度看,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共时的。真正的欣赏是对作品本身的玩味。你需要以一种闲适的心境,佐以清茶一杯,凝神于数尺单纯的墨迹之间,观其构图的繁简与疏密,墨色的浓淡、虚实的变化,点的组合与线的走势。你也许会渐渐感受到一种意趣,怦然心动,一种古典意义上的美感油然而生,同时神清气爽,有如遭遇一袭梅花的清香,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是几千年文化的淳酿。既然无需考虑历史,我们的目光便可随意地停留在任何一幅画上,
李方膺的墨梅图(图87):曲干、直枝上梅花数点,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画法,于简练之中,极见运笔的功力;画面浓淡、虚实、疏密的处理,造成了一种清雅的情趣。
金农之梅(图92),笔法极简,构图甚繁,看似随意,其实以浓、淡、白三分层次;繁花缀满,似笙管齐鸣,不见冬之萧瑟,却感春意盎然。金农自号“耻春老人”,其实人既不老,亦恋春情。春不在世态炎凉、四季冷暖,而在胸臆之间。金农的作品,大有现代西方艺术中“降低技术性”的味道。其画面的生机,主要是一种情绪的贯注。
罗聘是金农的弟子,为“扬州八怪”之一,其画风与金农相似而又自成特色。图102枝干似藤蔓,以梅花平衡构图,于苍劲之中隐含缠绵绯侧之情愫,枝干曲屈,花朵错落,布局开朗,进退自如,疏密有致。运笔也很有特色,有一种西画素描的光感,于是在平面的构图中更显一种空间深度。
马远的《梅花小品)(图4)匠心独运,数根虬枝,几点晦梅,突兀于烘云托月的背景之前,有一种孑然独立、上下求索的情调,有一种空灵之气和怅然之美。马远以简练的构图而得丰富的意韵,小品不亚大作。不过,这也许是笔者自作多情。有人曾问毕加索,他的一幅画中的红色牛头是否象征着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毕加索断然回答:“不,它就是一个红色的牛头。”对于马远的这幅小品,你可以不作任何意义上的联想,仅仅面对直观的形象,你的心灵便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震撼,也许,这便是一种纯粹美感。
陈绿的《玉免争清图》(图31)堪称古典绘画完美的典型。从构图上看,它是上下结构。底部墨浓干粗,略占三分之一,有力地支撑着画面。然后杈分两支,互相呼应延伸向上,如曲径通幽,绕道相合。顶部如纤纤玉手,托起一轮如蒙薄纱的明月。明月则将其清辉自上而下洒向画面,如此回还往复,严谨而富于变化,恰似一篇宏大的乐章的主旋律。右边直伸两条细枝,构成画面左右的均衡,并造成一种空间深度。这是构图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则是枝条交织、粗细、曲直、疏密,宛如配器。不是自然,胜似自然,无重叠之笔而有深远之感。第三层次当然是花了,点点簇簇,或隐或现,点缀于枝干之间,好似跳动的音符。而枝干上的斑结,或疾或徐,如深厚的鼓点,打出了乐章的节奏。月色朦胧、花枝摇曳,你仿佛已经闻到梅花的清芳,直撩拨得人心旌震颤。中国人素以“花前月下”借喻爱情。这幅画的确有一种爱情的情调:纯洁的追求、暖昧的骚动、缠绵的幻象、一种极深的敏感、丰富而精致得奢侈的情趣。至于技法的完美,则自不待言了。
本画册以梅花为一专题,收宋元以至明清的画梅精品入册,它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梅花画风的历史衍变,这种衍变从具体来说,它是不同时代不同气质的作画者的自然反映;扩而大之,它何尝不代表或暗示出时代风气在绘画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易于识别的形式、构图上,更重要的是反映于笔墨表现的技巧上,以及绘画材料的变化上。明清画梅之所以区别于宋元,除了时代所提供的人文环境不同之外,生宣纸的使用,也促成了明清文人大写意画风的流行。这对当今的中国画创作无疑是带有启示意义的。传统的笔墨表现精华固应认真体悟而深入把握,从创造这一角度讲,一个画种也可引起一个时代画风的根本性变革,因为当代人文环境提供给了画人以广泛施展才能的条件,这个条件主要表现在当代人文成果的广泛、便捷的传递上,绘画材料的广泛、丰富上,以及东西方绘画之精华皆可拿来为我所用上。